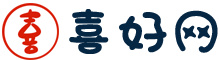2018年的夏天,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毕业的陈礼军,只身踏上了前往西藏林芝的火车,正式开启她的从教生涯。临行前,望着妈妈转身抹泪的背影,陈礼军在不舍之余暗下决心:这一趟,必定要“不虚此行”。
近年来,国内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人数有增无减,“到基层去”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大学生就业重心持续下沉,2023届本科生到县域就业的比例为27%,相比2019届增加了6%;同时,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也在上升。这些毕业生为什么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基层的热土上?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从教:去,还是留?在坚持中找到答案
到西藏去教书,这个在许多人听起来颇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却是陈礼军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姑娘心怀多年的梦想。初中时,陈礼军阅读了《酥油》一书,其中的支教故事使她备受触动,西藏这片土地也深深吸引着她。2018年,临近大学毕业的陈礼军得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开展面向广东专项招聘的消息,便立马报了名。
从南粤大地到青藏高原的这三千公里,一切都很顺利。机会来得刚刚好,大学期间在教学实践上已经积累一定经验的陈礼军也有一把抓住机会的能力;父母尽管难免担忧,但仍在一开始就选择支持女儿的梦想。就这样,陈礼军来到了林芝,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然而,梦想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现实的分量却也格外沉重。
首先是身体面临的挑战。“那时候学校还没有集中供暖,一到冬天,虽然有电热毯取暖,一旦关上,半夜总是会被冻醒。”陈礼军回忆,“刚到林芝的那半年,我经常感冒发烧、咳嗽、拉肚子。咳嗽还不容易痊愈,反反复复,体重甚至比毕业时的74斤还轻。”
不足74斤的身板,要保证一周二十几节的课时量,让彼时的陈礼军隐隐有些吃不消。更让她焦虑的是,此前她所有教学实践都是在广东的学情基础上积累的,但教学不是套万能公式,当地学情与广东大相径庭。当时,她接手的两个低年级班级在头一次质量监测中发挥很不理想,成绩和县里的标准差了几十分。“监测结果出来后,班主任老师还为孩子们的语文成绩特意找过我,大概是没想到孩子们在换了语文老师后,竟会考得那么差,我当时也被孩子们的成绩吓到了。”
身边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劝返声,一腔热血的陈礼军也开始有些拿不定主意了:西藏离广东实在太远,身体状况、工作压力等困难只能“云吐槽”,最后还得自己扛;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她也无法常常陪在双亲身侧。这样坚持,值不值得?
反复纠结的心理活动持续了四年多。这期间,虽然内心在去留之间“反复横跳”,但陈礼军在行动上却丝毫没有怠慢。她先是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将心中对教学事业的疑惑和对自己的怀疑一股脑儿倒给了老师。令她大受鼓舞的是,老师肯定了她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一句掷地有声的“这是一件长远的事,你放心去做”,像一颗定心丸,为陈礼军重新注入了能量。后来的日子里,在其他班的语文课甚至数学课上,都能经常看见陈礼军旁听学习的身影。同时,为了能更快地提升自己,她还积极参加了各级各类教学比赛,阅读名家名师的教育专著提升理论水平,理论实践两手抓。
让陈礼军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这份职业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的,是一次批改三年级孩子们写的作文。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很开心能成为陈老师的学生,陈老师让我的语文有了很大的提高。”陈礼军把这篇作文读了又读,看着孩子稚嫩的笔触,她红了眼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孩子们的反馈和进步,就是陈礼军的努力和坚持最响亮的回声,最开始低于全县标准几十分的那些孩子们,也在陈礼军的带领下一路勇往直前,成长到同类型班级的前几位。参加工作开始遇到的教学上的挑战,竟不知不觉成了陈礼军的成长跳板。另外,她还很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当地的教育硬件设施有了极大改善,教育局还大力推进与广东共同搭建的粤林两地“校地共建”项目的相关工作,增添了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输入,个人薪资也有较大幅度提升。渐渐的,去还是留,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选择。
“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有幸福感的老师”——大学期间,陈礼军对未来的自己这样期待着。在林芝从教六年有余,这一“希望”也已从将来时,逐渐走向了完成时。在与孩子们的“双向成长”中,她完成了从适应到融入的蜕变,不仅成为幸福的老师,还成为给孩子们带来幸福的老师。
行医:西部三年,暂时离开是为了更好相遇
2023年,陈礼军的第一届“开门弟子”顺利毕业。这群由陈礼军一步一步陪着长大、陪着进步的孩子们对陈礼军有着独特的意义,他们的成长,给了她做出最终选择的底气。面对又一个朋友的劝返,陈礼军以从未有过的坚定和自豪对朋友说:“不回去了,扎根了,教这里的孩子读书让我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教育带给我的幸福感,我很满足。”

这一年,也是罗华盛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服务的最后一年。离岗前夕,他参加了当地的一次中考减压活动。在“放飞梦想”环节,一架纸飞机不偏不倚落在了他的手心。展开纸飞机,命运般地,上面写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那一刻,他的心似乎与纸飞机的翅膀共振了:成为一名好医生,也是他的初心和梦想。
时间回到2020年。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热心志愿、热心基层的罗华盛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来到了普兰县,成为一名基层医生。普兰县是一座地理位置极其特殊的边陲小镇,坐落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小镇夹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道路交通崎岖又漫长,水、电、各类生活物资和医疗资源等都得之不易,发展也相对落后。罗华盛的住所不仅经常停电,还没有自来水,必须自己提水上五楼维持生活用水。
普兰的独特文化和发展情况还造成了当地民众普遍缺乏医疗常识,也不懂得如何自我健康管理。罗华盛在急症科的日常接诊中要花很多心思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有一次,医院接诊了一位26天大的新生儿,看着婴儿鼓得发亮的肚皮,火烧眉毛之际,罗华盛无意间一问的“有没有喂奶粉或母乳之外的东西”却成了救命的关键:原来,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了一种据说能够强身健体,婴儿却难以消化的特色小吃,糌粑。弄清了病因,这才成功救治了婴儿的肠梗阻。
这一方面警醒了罗华盛,为他积攒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罗华盛来到西藏后一直以来的困惑:自己到底能够为普兰,为基层带来什么?抓住机会,续签两次,尽可能留在这里久一点,踏踏实实做满三年,已经是彼时他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但把目光放长一些,罗华盛想为基层做的,远不止于此。
在这片西部世界,罗华盛收获了诸多感动。除了藏民们的淳朴和热情,令他最难以忘怀的,是一次出车送诊遇到的藏民。那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奶奶,当时已经因消化道出血出现比较严重的贫血情况,但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她始终牢牢护着工整佩戴在胸前的党员徽章,直到上级医院也未曾有一刻放松。如此强大的信仰的力量,深深震动、鼓舞了罗华盛。
然而,对于罗华盛而言,这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客观局限。想要成长为一名业务能力过硬的医务工作者,罗华盛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普兰在这方面并不是优选——相较来说,这里资源紧缺,整体发展水平也较低,个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三年,足够磨练出一个人坚强的意志,但“本领恐慌”却一直是罗华盛的心结。这个结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动解开,反而越绕越紧。自己没有足够的本事,又怎么能更好地为他人服务?
因此,离岗后,他选择再次回到校园,攻读研究生。“我仍然希望最终能够回到西部,或者说回到基层去做一番事业。”谈及对未来的规划,罗华盛坦言,“我本来就成长在基层,本科期间也一直在接触基层、服务基层,参加西部计划更是如此。但是,我希望以另外一种身份回到基层,建立自己的一个医疗团队,提升某个科室,甚至整体的医疗水平。”

育莲:择一业,精一事,当兴趣爱好“长”成毕生事业
或教书育人,或救死扶伤,陈礼军和罗华盛都早早找到了各自梦想的土壤,并持之以恒地耕耘着。择一业,精一事,育莲人李子俊亦是如此。而他这一业一事,甚至开启得更早——今年,是三十岁的李子俊养莲的第二十个年头。
“我觉得小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如果小时候因为机缘巧合,接触到一个事物,有可能发展成一种终生兴趣。”李子俊与睡莲的缘分始于幼儿园时期——经常被奶奶带着逛公园的他,迷上了盛放池塘中的各色睡莲。光是赏莲还不够,小学三年级,他就开始在当地花市买些叫不出名字的荷花养着玩;四年级,他第一次向南京艺莲苑邮购了十几个有名有姓的荷花和睡莲品种;种植的品种丰富了,小李子俊又冒出了新点子,他开始尝试杂交育种,培育独有的新品种。
那时,九楼家中的天台就是李子俊的宝地。养莲用的五十多个蓝色塑料桶和几十吨泥土,都由他的一双手,一趟一趟搬上去;父母不支持,他就六七点钟偷偷起来爬上天台,趁八点前上学的时间,见缝插针做自己的育种工作;育种少不了资金,就靠自己从零花钱里一点一点省,还不够,那再想法子一点一点挣;很多时候种子种下了,花却不开,或花开了,复种却难以成活,他就去进修专业知识,憋着一股气再试再种。“我一直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办法总比困难多,兴趣是李子俊最大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李子俊培育出了他的第一个睡莲新品种“樱桃轰隆”,一年后,18岁的他再度育成新品种“侦探艾丽卡”。这一以他钟爱的侦探小说人物命名的品种,不仅在第十届世界睡莲大赛上一举夺得两枚奖牌,还陆续被种植到了20多个国家。
同是18岁那年,李子俊考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读园林专业。大学期间,他在育莲之路上继续“飞奔”,参加了许多国际比赛,还加入了国际睡莲水景园艺协会。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多年来自己摸索和积累的经验,为李子俊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于是,2017年顺利毕业后,李子俊谢绝了北京的研究机构和国外几家苗圃公司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将兴趣发展为事业,专心育莲。
再三衡量之下,李子俊选择带着他的睡莲培植技术从广州来到佛山高明,与当地农民联手开发农旅项目,投身大型花卉产业园和农旅休闲胜地的建设。其中,他负责水生植物的养护管理,兼顾培育水生花卉。亲力亲为引进优良品种,培育新品种……经过多年的努力,李子俊在此打造了三大睡莲园区,包括占地5亩供游客观赏的水生植物园,以及各占地3亩的新品种培育区和品种资源库。
昔日栖身楼宇天台的“李式睡莲”,如今安然盛放在园区内一个个造型别致、种植专用的大缸中,莲开千色,花呈百态;而当初说李子俊“不务正业”的妈妈,也改了口,笑称儿子“可能是被贬到凡间的瑶池神仙”。
作为育莲人,李子俊仍在路上。他希望,培育在大缸中的种苗能够开枝散叶,大面积推广种植,顺利对接市场需求,使更多的睡莲爱好者能观赏到自己培育的新品种睡莲;同时,也竭尽所能,为推进农旅融合、促进当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到村:从大山到更深的大山,在随遇而安中找到意义
相比之下,静茹(化名)进入基层,进入大山,更多的是机缘。
2022年,考研失败的静茹马不停蹄地转战各类事业编和教师招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了解到了“乡村振兴万人计划”。考试时间迫在眉睫,静茹选择放手一搏,“极限”备考。报名、笔试、体测、面试、体检、公示……终于,她有惊无险地“卡位上岸”了——总共招15个人,静茹是第14名。
“卡位”是一种幸运,但却也可能意味着被动。选岗只选乡镇,到了乡镇再分村,具体按录取名次依次选。这样一来,轮到静茹时,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乡镇,也是最远的一个。那里距离县城八十公里,交通非常不方便,开车都要翻山越岭一个半小时,偏偏静茹的工作免不了常常来回奔波。晴天也就罢了,一碰上下雨才头大。“有一回下雨路不通,走了一下午,四个多小时才到乡镇。下村的路更是,那泥泞的,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这是去上班的路。”
静茹担任的是村支书助理一职,笼统地说就是帮村干部做一些村里的事情,但要掰着指头仔细数起来,两只手都不够用:要为村内外出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稳岗补贴,要为在村居住人员整理发放地力补贴、庭院经济、特色产业奖补;要为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人协助办理低保、特困、残疾,临时救助,还要跑撂荒地、入户走访、经济普查,不胜枚举。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内容、极其偏僻的工作地点,刚上岗时,说没有落差感,不迷茫、不失落,是假的。那时候下村路上,静茹每每坐在车里望着窗外出神,目之所及除了一座座山,就是拐不完的弯路,单调重复的景色给人一种永远也走不出这片山区的错觉。此时,她总会在心里问自己: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我出生农村,小时候人人都说,好好读书是为了走出大山,可是好不容易考出了大山,进入了大学,毕业后却考进了更深的大山。”静茹不禁有些迷茫:兜兜转转,怎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甚至更退了几步?
“上岸”不易,静茹安慰自己,在这五年的服务期里“既来之,则安之”。心态“炸”一会儿,还是把自己“拼”好了,继续干。身边年龄相仿的同事有的离开了,也有的和自己一样留了下来。人来人往间,在随遇而安的过程中,静茹逐渐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归属感。
尽管静茹负责的都是些“小事”,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都是最要紧的实事。“记得我们村有个脱贫户,耕地的时候不小心被枣枝戳伤了眼睛,干不成活了。我和村委赶紧帮他办理了残疾证,又帮他申请了低保,最终实现了每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总算是有个兜底。”谈起这份工作让她感到备有成就感的瞬间,静茹分享道,“我最知道农民靠天吃饭的不易,现在沉下身子为他们干点小事,为有需要的人们做点事,真正帮助到他们的时候,确实感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村民们也时刻以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热爱之心治愈着静茹。去村里入户时,静茹曾碰到一户人家,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他们答“没什么困难,我们都有手有脚的,需要钱了就自己努力干活,总会越来越好的”。这短短一句大白话,却让静茹记了很久。
到村一年之际,静茹在社交平台上写了一篇长长的心得。写到一年前的选岗大会,自己别无选择地来了“大家都不想来”的乡镇时,她加了个带点无奈的“笑哭”表情。但紧接着下一句就是,“现在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转眼间,静茹已经到村两年多了。当被问起“是否满意目前的工作状态”时,静茹没有犹豫,直言:“满意的,我很感恩我所拥有的一切。”从大山到更深的大山,并不是倒退。走出大山,是为了去见识更大的世界,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人;回到大山,则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和更多人一同创造更好的生活。“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值得。”静茹说。
如今,陈礼军仍在雪域高原的热土上完成自己的教育之梦;罗华盛以“成为学科带头人,回到基层”为目标继续深造;李子俊在睡莲新品种培育之外,还致力于发掘睡莲的其他价值,努力将睡莲的清香送进千家万户;静茹则心存期待与珍惜,继续着她的驻村日常,琢磨着要考一个在职研究生。基层是一片广阔的沃土,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尽管方向不同,但同样做到了“不虚此行”。
文|记者 孙唯 实习生 袁辰悦
图|受访者提供
本文链接:http://www.xihao.site/showinfo-4-12513.html毕业就业旅程中,他们选择了一处别样的“人生逆旅”